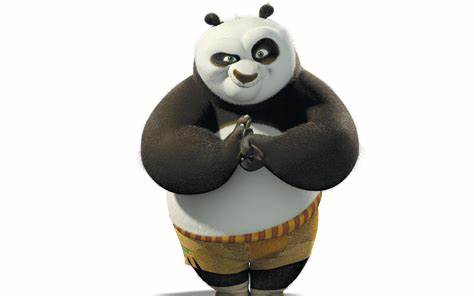仲夏当午的灿烂阳光下,身着深色单衣的中年男子和身着浅色单衣的年轻后生一边擦拭着脸颊上的汗水,一边用手中的耘锄铲去瓜田里同样茁壮生长的杂草。天气还未到最热的时候,可头顶的日头直晒到人身上,真个是“汗滴禾下土”。老天爷要是能送来一阵风,哪怕是风带着雨也好啊!淋湿了岂不更凉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年男子已经历过了读书求学的年纪。他曾经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礼乐娴熟、志在指点社稷的狂放书生。怎奈何彼时礼坏乐崩,佞臣当道,也只好放弃仕途,归隐乡间,春种秋收,倒也衣食无忧。虽如此,但眉宇间已寻不到当年的踌躇满志,只可见岁月风蚀的坚毅和些许残存的舍我其谁的豪情。
年轻后生正值弱冠之年。平日里师从大贤,研习诗书礼乐,是闻名乡里的孝贤书生。农活对于他来说,若说娴熟,那真还差着一大截。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还真是起了一阵微风。后生停下耘锄,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见中年男子并没有歇息的意思,也顾不得筋骨已然疲惫,俯身继续劳作。
也不知汗水模糊了双眼,还是那日头晒得头晕。只听“咔哧”一声,后生定睛一看,不好!手中的耘锄搂掉了一溜瓜秧!
中年男子看到后生愣在那里,不知何故。过来一瞧,好家伙!杂草没锄掉,瓜秧倒是搂掉了不少!也不知这瓜秧是何宝物(肯定不是西瓜秧),招致中年男子怒火中烧。说时迟、那时快,中年男子抄起耘锄,杆在前,头在后,向后生背上打来。后生见状,头一缩,眼一闭,而身子却杵在那丝毫未动。伴随着的“砰!”一声闷响,锄头杆重重地打在后生的背上。后生一头栽倒,人事不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年男子见状,耘锄扔在一旁,蒙圈加后悔。怎么会下手这么重!
好在年轻人体格还算好,再者刚才那一下并未打中要害部位。过了片刻,年轻后生醒来。起身后,拍拍身上的尘土,脸上带着歉意还有那么一丝开心,向中年男子拜了一拜,说道:“刚才都是我不对,惹您老生气了。父亲大人您教育的对,以后小儿定是不敢如此莽撞了。您刚才用力教训儿子,您老人家不碍事吧?”
中年男子脸上的怒色已褪去了不少,加之心中尚有自责,并未作声,转过身,捡起耘锄,头也不回地往家中走去。年轻后生愣了愣神,也紧跟在中年男子身后。
看到这里,各位看官应该大概有个眉目了。
不错,原来这是父子俩,一起在瓜田里劳作。结果因儿子的不小心,被老爹一锄头杆打晕在地。
不过这个事还没结束。接下来如何呢?请耐心往下看。
回到家中,中年男子自去歇息。年轻后生却顾不得劳累与疼痛,进入房中,摆好木琴,边弹边唱。这是要干什么呢?
年轻人是想让父亲知道:父亲责打我是对的。我身体没事,能弹能唱,而且还很开心。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件事很快在乡里传开了,他的老师也知道了此事。老师很是生气,或者说可以用愤怒一词来形容。于是老师对其他学生说:“这家伙要是再来上学,坚决不能让他进来。

次日,年轻后生继续到学堂去学习诗书礼乐。
到了学堂门口,大家都拦着不让他进。他很纳闷,问了缘由,得知是老师把他除名了,很是吃惊:认为自己做得没错,老师怎么能把我除名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管怎么说,老师就是不见他。软磨硬泡,一个资历较深的同学算是答应帮他去向老师求求情。老师怎么说呢?
老师的大概意思是说:从前,舜的父亲脾气也很暴躁,并且总是看舜不顺眼。但是,舜的父亲让舜做事的时候,舜肯定能及时来到父亲跟前;而父亲发怒要杀他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避开。这样,他父亲就不会背上杀子的罪名。而舜也不失孝子的名声。我这个学生,他父亲暴怒之下拿大棍子打他,他躲都不躲。如果被打死了,那他就是陷其父于不义,这才是大不孝。他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无辜杀害了天子的子民,该是什么样的罪?
图片来源于网络
年轻后生得知老师说的这些话后,算是恍然大悟,说道: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深刻反省了一番,又再次登门作了深刻检讨,老师才算原谅了他。
各位看官,这个事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并非在下的杜撰,而是尽己拙劣所能还原了一段古籍典故。这就是《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的曾子(曾参,孔子得意门生之一,注重修身、自省,后世尊为“宗圣”)年轻时候为彰显孝道所做的一件事。
何谓孝?
图片来源于网络
孝是中华民族的一项美德,是晚辈对长辈的敬重、关爱和尽心尽力。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是非对错地顺从长辈,更不是宋明之后所谓儒学大家倡导的用生命去兑现的“孝”。这些,都是愚蠢的孝道。
正如孔老夫子对曾子所说的:你父亲怒气冲冲可能会伤你性命的时候,你躲都不躲,那不是“孝”,而是大不孝!
图片来源于网络
注:《孔子家语·六本》(节选)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
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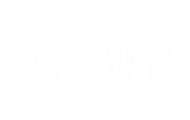
 阿壮博客
阿壮博客